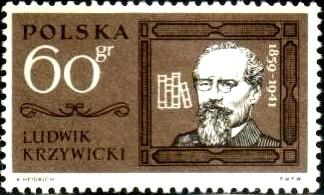Seizer, S. (1995). Paradoxes of visibility in the field: Rites of queer passage in anthropology. Public Culture, 8(1), 73-100.
大约是 1994 年,Susan Seizer 在印度 Maduri 研究泰米尔社区的舞台表演。这篇文章和她的项目没太大关系,而是讲述了作为美国女同性恋的 Susan 和她的女友 Kate 在印度的一些奇特经历。
Maduri 是印度南部的一个小城,或者说是一个大点的村子。Susan 和一个表演者家庭(妻子是演员,丈夫是乐手,两个青春期的女儿)合住在一套小单元房里。条件很差,饮水要自己挑,虽然 Susan 和他们各付了一间房的房租,然而每天晚上,按照印度的习俗,是按照性别分房睡的。于是 Susan 和三个女人睡一间,一个男人独自睡一间,房门都开着,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。女人们睡觉时也永远穿着衣服,四个女人睡的很挤,肢体接触,鼻子埋到旁边人的头发里,没有人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,当地人一生就是这样度过。
在印度,女性之间的亲密,无论是物理接触还是情感依赖,是一种被社会所接受乃至赞赏的行为。女人们永远紧挨在一起,互相试衣服,不时地亲密接触。拒绝这种亲密的人,反而会被认为势利或者刻薄。但这样的亲密行为完全和同性恋无关,当地文化中没有女同性恋的概念。泰米尔语里无法表达 lesbian 这个词,却专门有一个词(tōl̲i)用来描述女性的亲密同性伴侣。这一度让 Susan 很困扰,一方面,这种女性之间的接触,对一个美国 lesbian 来说,感觉更像是性接触;另一方面,这种女性之间的亲密情感对 Susan 来说也很舒适,然而这种模式下待久了,确实会感觉被这种情感压抑了自己其它欲望……
Kate 从美国来陪 Susan,然而她在 Maduri 待了很短时间就受不了了,跑到几百公里外的大城市 Madras(钦奈)住着。Kate 不是做人类学的,让她无法忍受的不光是恶劣环境、和当地女人们没有隐私地睡在一起,也包括当地文化中这种女性之间的亲近。——然而 Susan 和 Kate 被当地人认为是非常亲密的 tōl̲i 从而认为她们心地善良(反正当地人不知道什么是 lesbian,她们又没隐私空间去做什么更进一步的……)。Kate 更乐于维持自己原本的文化习惯,以一种支配的视角去看待当地文化。她在 Madras 参加各种学术政治讨论,女权和 LGBT 集会,每周大使馆的活动。后来 Kate 在 Madras 的高尚社区,找到了一份替人看家(housesitting)的工作,于是 Susan 决定来和 Kate 在高尚小屋里一起住三个月。
小屋的原主人是一对夫妇,有 7 个仆人,即使主人走了,仆人也会来定期打扫。所以 Kate 发现大家似乎对 housesitting 这份工作的理解并不一样,她们其实不用做清洁,不用剪草坪,只是在主人离开期间,占着这个用来和仆人们沟通的上层阶级的位子。于是她们更开心了。Kate 把 Susan 接到小屋,二人在楼上卧室里脱了衣服(终于能脱衣服了!)拥吻(终于有隐私了!),然后,突然,卧室的门被女仆推开。
一片尖叫声后, lesbian 们穿好衣服,来到楼下。女仆用当地俚语凶狠地责备她们:
「我要刷楼上地板了!你们在房间做什么?为什么我按门铃你们不开门?」
「那个门铃声小的就像鸟叫一样……你不是下午才来么?」
「我每天来两次,早上七点,和下午。」
「没必要啊……」
「不,有必要。」
女仆叫 Angela,是基督徒,那种在印度典型的,通过信教来摆脱自己低等种姓的基督徒。于是 Angela 每天早上七点出现,把她们轰起床,把已经很干净的房间清洁一遍,然后洗自家带的衣服。女同们又一次失去了隐私,被搞的神经衰弱,成天把鸟叫幻听成门铃。她们试图和 Angela 改善关系,但每次尝试沟通都不欢而散。Angela 对她们的这种粗暴态度,其实作为仆人来说,非常少见,但 Angela 又对原房东非常恭敬和推崇。想必是虽然雇了7个仆人但崇尚平权的房东让仆人们有了更多表述的自由,以及房东的社交圈让仆人不再对外国人觉得新鲜,把她们视为占用了主人空间来乱搞的恶劣白人……
最终 lesbian 们忍无可忍,请了个调解人:原房东值得信任的密友,一个崇尚女权的婆罗门家庭主妇(和双方都有共同点了)。婆罗门主妇向 Angela 解释外国人需要隐私,不想这么早起床。最终大家向女佣完整地解释了一遍女同性恋文化,这在西方很正常,我们理解这会被基督徒厌恶,但请不要在我们做爱的时候砸门进来ok?
然而,经过调解人的沟通,Kate 和 Susan 发现,Angela 对 lesbian 神马的完全没概念,她关注的是更重要的事情:你们两个外国人,把楼上房间的门都关了,一起在房间里待几个小时,你们一定是在——
铸 假 币 !!!
。。。。。。
是啊,在当地人的眼里,所谓卧室里的隐私,其实和财富的关联,远远大于什么性癖、人权……白人来印度就是一个增加自己财富的过程,白人之间的每一次甜蜜接触,都会让他们变得富有。Angela 推开卧室门看到的,不是亲密性爱,而是由个人经验和主观意识构成的散漫网络。Susan 最后甚至有点感动,在女性身份和价值很难在脱离男性的环境中被评估的今天,只有 Angela 认为她们是单纯做什么重要的事情,把 lesbian 在彼此身体中寻觅的东西,翻译成了一种像货币一样直观的价值。女性的身体成为了压铸 lesbian 自身意义、转换自身价值的资本机器。某种意义上讲,铸钱,难道不正是对我们晚期资本主义 lesbian 的很好的隐喻么?